麻木的反義詞 荒誕:現代性背景下的人生境況與在世體驗
更新時間:2024-06-24 08:39:04作者:佚名
阿爾貝·加繆(1913年11月7日-1960年1月4日)
01
—
荒謬無處不在
《莊子·田子方》中有一則關于孔子意味深長的故事,說有一天孔子終于見到了他特別敬佩的思想家文伯學子,但他只看了一眼,不發一語。后來麻木的反義詞,迷茫的子路問老師為什么這樣做,孔子回答說:“這樣的人,道在眼中,無話可說。”在孔子看來,像文伯學子這樣有道的人,一眼就能知道,不需要用語言。在今天流傳下來的加繆的照片中,我們也能看到一個眼神深邃的哲學家形象,一眼就知道他不是普通人。正是加繆,在歷史上第一次把荒誕上升到哲學和美學的高度,對后來的所有文藝流派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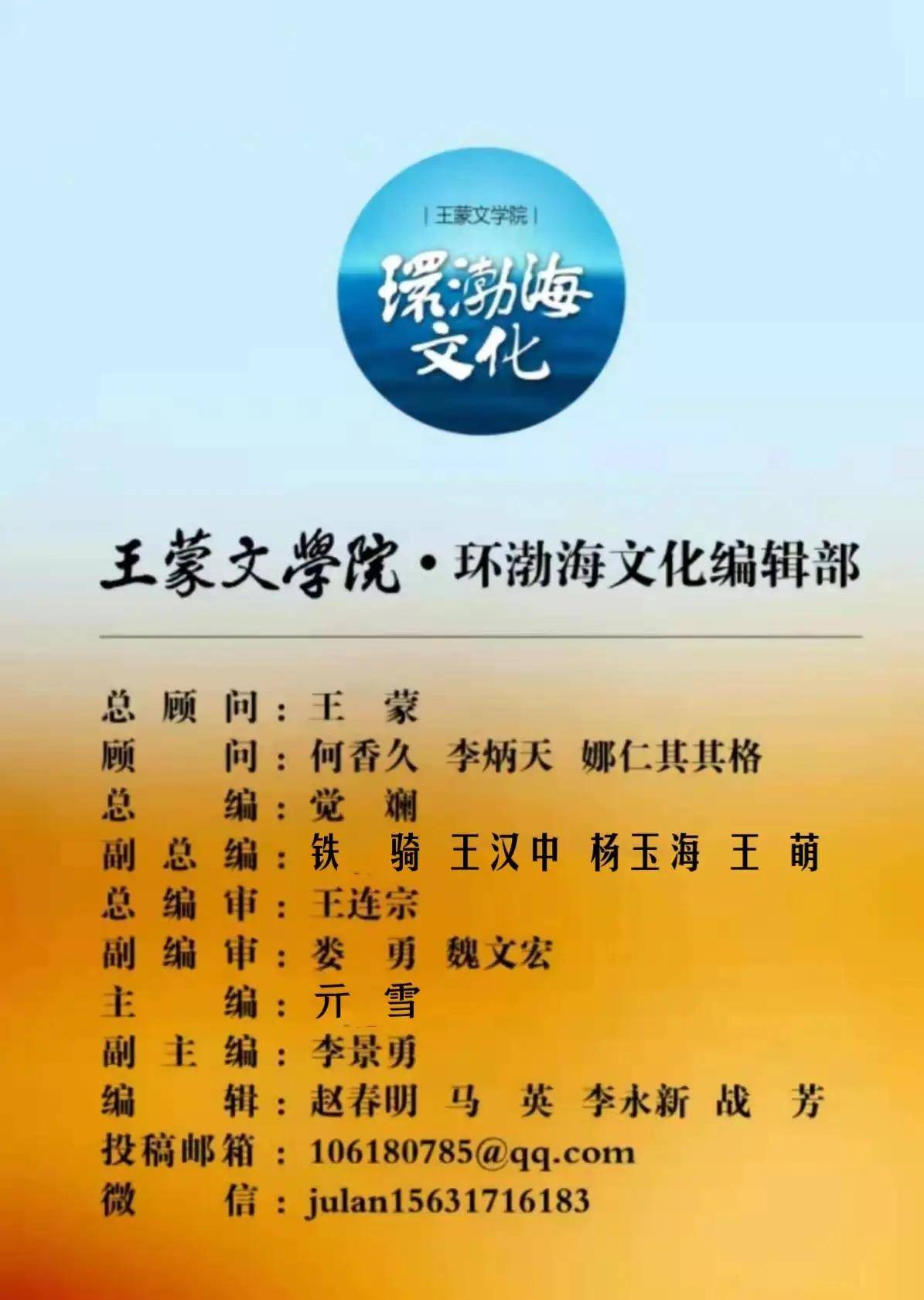
西西弗斯神話
加繆在著名的哲學論文《西西弗斯神話》(1942)中,對荒誕進行了精妙而獨特的論述。首先,他明確地把荒誕的無所不在認定為一種感覺:荒誕感會在任何一條街道上撲面而來。這種荒誕感赤裸得讓人不堪忍受,明亮卻又暗淡,難以捉摸。更為荒誕的是,一切偉大的行動和思想,往往都有著微不足道的起源。偉大的作品往往誕生在街頭的拐角處,或是酒店狹小的大廳里。歸根結底,機械的日常生活所帶來的無聊、乏味和焦慮,引發了這種生活荒誕感,由此產生了加繆那篇著名的文本,他在文中用現代人生活中最普通的畫面,精彩地表達了現代人日常生活狀態的荒誕性:
起床,坐電車,工作四個小時,吃飯,睡覺;周一,周二,周三,周四,周五,周六,以同樣的節奏重復。但有一天,“為什么”的問題浮現在腦海中,一切就在這種略帶意外的無聊中開始了。
當然,作為文學大師的加繆并不滿足于通過散文來闡釋荒誕,他同一時期創作的著名小說《局外人》(1942)讓人們更加真實地認識和觸及荒誕的真面目。小說主人公默爾索作為生活中的“局外人”,深感生活的虛幻、枯燥和乏味,對外界的一切都漠不關心,他自己成了一個陌生人,母親的去世、愛人的愛情都激不起他內心的波瀾。相信讀過《局外人》的讀者都不會忘記它那著名的開篇:“今天,我的母親去世了。也許是昨天,我不知道。”在這里,默爾索對自己的生活抱有冷漠的態度——這是人類意識到自身存在的荒誕性,卻又被迫無奈地采取的一種消極的人生態度。冷漠的外表下,體現著對世界荒誕本質的透徹理解。 然而,正是對荒誕性的覺醒,才使得默爾索的麻木、被動、冷漠獲得了高度的哲學意義,荒誕感被擬人化了。
于是,在一個上帝在歷史上退出舞臺的世界里,荒誕就爆發了。 薩特的《惡心》(1938)以日記體思考世界的偶然性和不可知性,博爾赫斯的《圓形廢墟》(1944)交織著現實與虛構、幻覺與夢境,貝克特的《等待戈多》(1953)雖然對話如夢似幻,但始終在進行中,尤奈斯庫的《犀牛》(1960)在科幻氣質與狂熱敘事的結合下,人淪為動物,約瑟夫·海勒的《第二十二條軍規》(1961)“只有瘋子才不被允許飛翔”……荒誕不斷以絕望、惡心、虛無、異化、黑色幽默等各種形式出現,如同川劇中的變臉,讓人眼花繚亂,但它們對荒誕的表達都指向同一個中心,那就是意義。在加繆的《局外人》中,這種擬人化、高度哲理性的荒誕達到了文學的頂峰。在后世讀者的心目中,《局外人》就是荒誕文學的巔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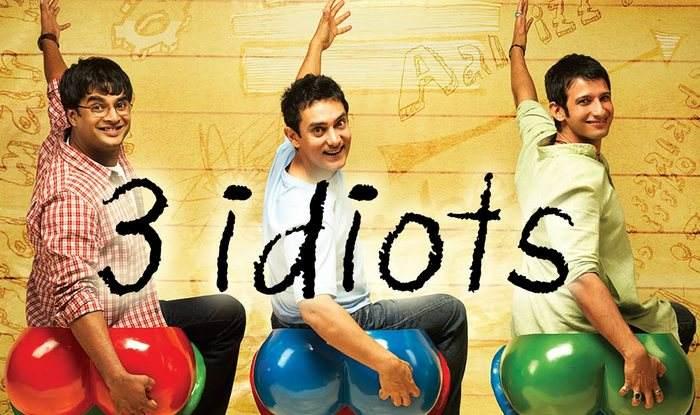
在加繆建構的世界里,人的存在不再是有目的的、必然的、神圣的、無限的,無目的性、偶然性、瑣碎性、有限性成為了存在的真相。于是,我們看到以加繆為代表的荒誕文學無情地抹殺了詩意的神話,殘酷地揭示了人存在的真相——存在被貶低為生存,而這種生存才是生存的唯一基礎。這無疑沉重地打擊了人的自尊心,用非理性的重炮摧毀了人類千百年來構建的形而上的精神大廈。殘酷的是,這些特征一直延續到21世紀的今天,并在碎片化的微時代呈現出放大的趨勢。
02
—
我反抗故我存在
加繆的偉大之處在于,他不僅深刻理解了荒誕的本質,還為那些在荒誕中掙扎的人指出了一條道路:反抗。在加繆看來,荒誕應該用反抗來反抗,人類只有在與其陰暗面的永恒斗爭中,才能重拾生存的尊嚴。沒有這樣的反抗,荒誕只能讓人走向自殺,那將只是一種逃避和投降。因此,加繆有著偉大的抱負,他希望走出個人孤獨的處境(雖然他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孤獨的個體),與更廣大的人類融為一體——他要把單個的“我”拓展到集體的“我們”,把個人獨自的內心斗爭引向一群人的綜合斗爭。于是他寫下了那句震耳欲聾的名言:“我反抗,故我們存在”。這種反抗將使一個人走出自己的孤獨,走出個人邏輯的困境。 他依然為自己而戰,同時也在與他人一起戰斗、為他人而戰,這是加繆對人類的偉大熱愛,也是他真正的理想主義。

“局外人”
明白了這一點之后,我們再回頭看他的《局外人》時,就會有更多同情的理解和共鳴。一個人與周圍世界的疏離、異化和不相容,源自他對現行社會規范的蔑視,從而成為社會中的“異類”,這正是加繆所提倡的“反抗哲學”。他說:“一個可以用反常邏輯來解釋的世界,依然是一個熟悉的世界,但在一個突然被剝奪了幻想和光明的宇宙中,人們卻感覺自己像局外人……這種人與生活的分離,演員與布景的分離,就是荒誕感。荒誕本質上是一種分裂,它并不存在于兩個對立因素的任何一方,它產生于它們之間的對立……它不在人,也不在世界,而是在二者的共存中。”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,荒誕感并不是冷漠的近鄰,而是它的反義詞,正如加繆在《局外人》序言中對默爾索的正面評價:“他遠非冷漠,他有著執著而深沉的激情,對絕對、對真實的激情。”
我認為,加繆所有作品(無論是小說、戲劇還是散文)的核心都在于這種反抗的哲學,這種反抗讓加繆為這個毫無意義、荒誕不經的世界注入了意義,正如他動情地坦白:“我一直堅持認為,這個世界沒有非凡的意義。但我知道,這個世界上有一些東西是有意義的,那就是人,因為人類是唯一提出了生命意義的生物。”因此,加繆一直在尋找人類身上不可磨滅的人性,這是他一生為之奮斗的目標。如此說來,瑞典皇家學院授予加繆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詞可以說是一語中的:“就加繆而言,他已經遠遠逃脫了虛無主義。他的嚴肅而嚴厲的沉思,試圖重建被破壞的東西,讓正義在這個沒有正義的世界中成為可能,都使他成為一個人文主義者。” 1957年,加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,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講,題為《藝術家和他的時代》。演講結尾的話語震耳欲聾:
美……無論從長遠還是短期來看,都只能服務于人類的苦難和自由……這種希望是由成千上萬的孤??獨靈魂所激發、激發和維持的,他們的行動和工作每天都在否定歷史的界限和最粗野的表象,為的是讓瞬間的光芒照耀出一直受到威脅的真理,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痛苦和歡樂中為所有人建立了這一真理。
讀過加繆作品的人,都會很容易認同蘇珊·桑塔格在《加繆日記》一文中對他的評價:“卡夫卡讓人憐憫和恐懼,喬伊斯讓人欽佩,普魯斯特和紀德讓人尊敬,但除了加繆,我想不出還有哪位現代作家能讓人愛。”用加繆自己的話說,“藝術家真正捍衛自己,是出于對同伴的愛。”這種深沉的愛,把加繆與世界、與他人、與自己聯系在一起,使他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一個局外人,而是一個反叛者,為每個人射出了“最強的自由之箭”。
要知道,出生于阿爾及利亞的加繆,不僅支持阿拉伯人追求平等生活,而且從1937年到1957年整整二十年的時間里,一直關注著阿拉伯人的生存狀況。他比大多數法國知識分子更了解他們的苦難,對法國政府政策的無能更為憤慨。加繆承認阿拉伯人對獨立的要求,但他無法接受他們為實現這一目標所采取的手段:對無辜民眾發動恐怖襲擊。加繆堅持認為,真正的正義不會誕生于暴力,而必須來自人與人之間的友誼和信任。在今天這個戰亂頻仍的動蕩時代(尤其是最近以巴沖突再度抬頭),加繆的洞見依然閃耀著真理的光芒。對此,加繆一生的摯友兼對手保羅·薩特在悼念加繆的悼詞中表達得最為準確和動人:

在這個世紀里,他頂住了歷史的浪潮,繼承了法國文學中歷史悠久的警世文學,這也許是法國文學的最大特色。他以頑固、狹隘而純粹、嚴厲而感性的人文主義,與這個時代的巨大而畸形的事件進行了一場不確定的斗爭。但反過來,他又以一貫的拒絕,重新確立了我們這個時代中心的道德價值,反對馬基雅維利主義和唯物主義的現實主義。
03
—
地中海思想
對于出生在北非的加繆來說,西北歐和地中海構成了兩個截然相反的世界。在西北歐陰郁、暴虐、絕望的世界里,徹底的荒誕、冷漠和絕望吞噬著人類的存在。而在地中海,感官的歡愉和輝煌讓人時刻感受到生命的力量。于是,我們看到成年后的加繆不斷回到故鄉阿爾及爾,并驕傲地告訴人們:“你會愛上阿爾及爾,因為這里的人一眼就能看到的東西:每個街角都能看到的大海,灼熱的陽光,人們膚色的美麗,而在這種肆意的暴露和犧牲中,總有一絲淡淡的芬芳在飄蕩。在巴黎,你會懷念那遼闊的空間和飛翔的鳥兒的翅膀;在這里,至少你心滿意足,別無所求,你可以真正衡量自己的財富。”

反叛者
這就是加繆在《反抗者》(1951)中極力推崇的“地中海思想”的由來。這種思想的精髓在于堅守對人的信仰,熱愛生活,贊美世界和生活的美好,但又對世界的陰暗面——荒謬性有著清醒的認識,拒絕盲目的樂觀主義。不難發現,“地中海思想”吸收了古希臘人生智慧中中庸適度的思想,這與中國傳統儒家和道家的觀點如出一轍。古希臘人始終堅守極限的理念,不把任何事物推向極端,無論是神圣的事物,還是人類的理性。這與我國古代哲學家老子告誡世人,人走到極端就要反其道而行之的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。 因此《文學雜志》主編余讓-路易如此形容:在《反抗者》中,我們看到了加繆的“希臘心態”,它歌頌地中海的陽光與大海,相信對生活的熱愛能趕走對生活的絕望,始終堅持與現實中的各種陰影和邪惡作斗爭,始終向往一個充滿地中海光芒的世界。
是的,這位絕世俊美的男子有著一顆“希臘心”。他無數次贊美地中海的陽光和大海,相信激情和愛情能驅走絕望。他多少次回到地中海礁石上的蒂帕薩古城,坐在港口的小咖啡館里,望著遠處的地中海:“茫茫大海在正午沉寂,一切美好的生靈都會自然而然地為自己的美而感到自豪,而我們眼前的世界,四面八方,都在展現著這種自豪。面對這樣的世界,……我為什么要否定生命的喜悅?……我不禁要問,這世間的一切都在給予我生命的驕傲。在蒂帕薩,我所看到的就是我所相信的,我不會固執地否定我用手觸摸的、用嘴唇親吻的。”世間沒有超越的幸福,黎明和黃昏之外也沒有永恒的生命。從荒誕到叛逆,除了陽光、親吻和原野的芬芳,一切都顯得微不足道。
加繆曾在散文《謎》(1950)中寫道:“我憑著對太陽本能的忠誠,我出生在陽光明媚的土地上,那里的人們千百年來懂得向生命致敬,哪怕是在痛苦中。”正是這種“地中海思想”,使得加繆雖然早年生活飽受磨難,卻從不抱怨世事,而是盡情享受大自然的饋贈。同時,他的人生觀是積極的,他不抱怨,他從未對人性失望過。“人身上值得稱贊的地方比可鄙的地方多。”“我關心人,我從不瞧不起人類……我作品的核心,始終有一個不朽的太陽。”這個不朽的太陽麻木的反義詞,源自他在北非地中海沿岸的生活經歷。 它串聯起其全部作品的內心激情,將人類在陽光下的真實處境揭露出來,進而層層摧毀自欺欺人的帷幕,直指人性、人生乃至世界的根本荒謬,進而逐漸引導有意識的新人通過反抗走上自由之路。
如今,以加繆為代表的荒誕文學熱潮早已褪去,但荒誕依然隨處可見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中、世界的每個角落,并在碎片化、人工智能時代不斷變換著各種面貌。這不是世界末日,而是人類在經歷了理性的第二次崛起和非理性的蓬勃發展之后,面對世界的清醒意識和從容態度。當然,面對無處不在的荒誕,冷眼旁觀、一笑置之是遠遠不夠的。如果說荒誕的人生和世界是一道陰影,那么荒誕本身的探討終將把我們引回陽光。因此,加繆反抗自殺的哲學在任何時代都是彌足珍貴的,成為他留給后人的不朽遺產。換言之,在荒誕中尋找永恒,從虛無中產生意義,從無聊中借用靈感,在閑暇中追問是否有創新,是貫穿現代人一生的現實課題。
微時代最佳圖書榜單